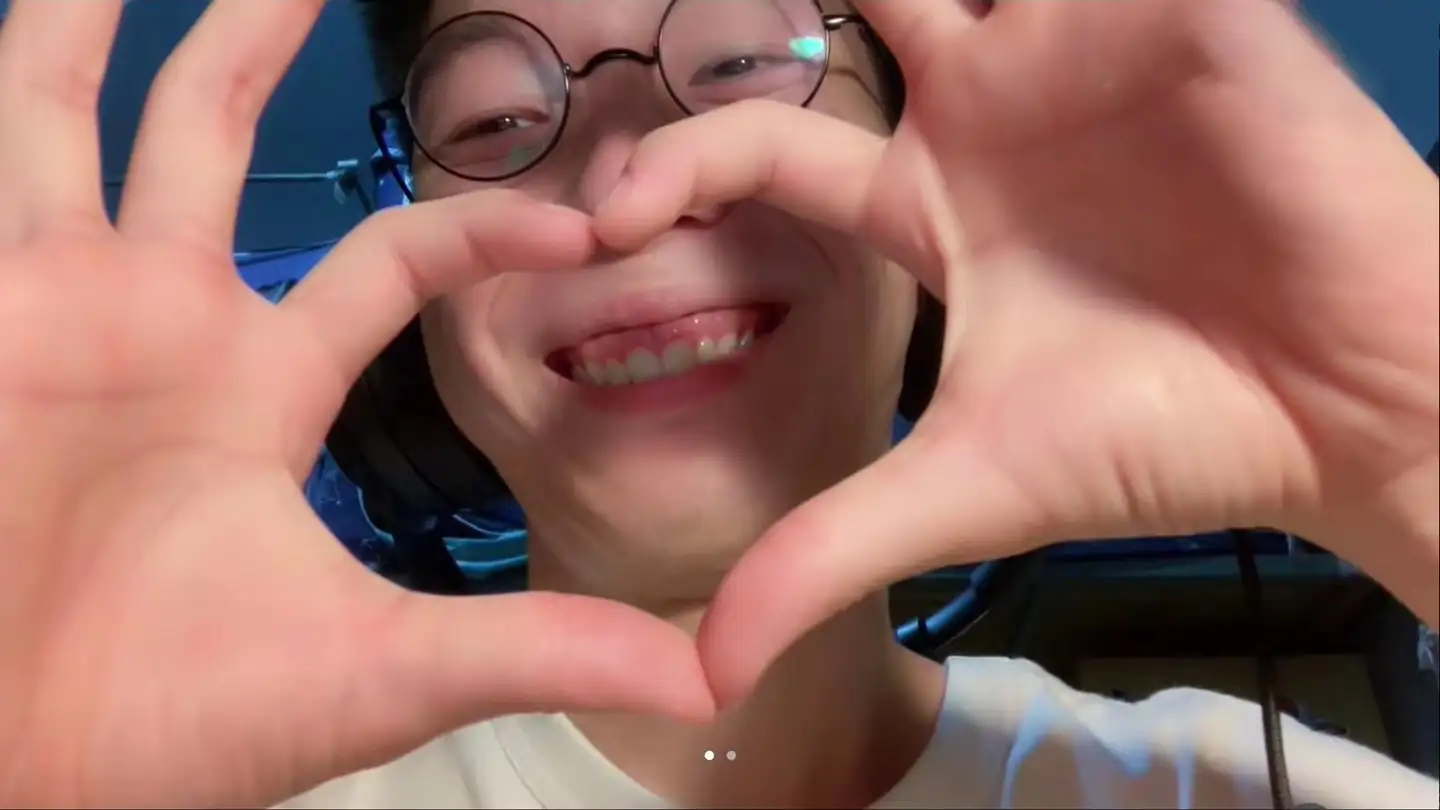哲学
第一次听完了一整节哲学课,课程很浅薄但是给予了非常多的思考,我不想让这些,也许还挺有价值的思考就这样忘却,所以选择记录下我学习的过程。
第一部分 我需要学什么?
课程的开始首先是一个疑问“我能否免于死亡?”似乎这个答案有着呼之欲出的答案,但我们也不得不多思考一点——假设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灵魂”,问题的答案还那么显而易见吗?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那么在没有灵魂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就一定会死亡呢?死亡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谈起死亡是否只有害处而没有任何利好?以及在弄清楚了上述问题后,我们又该以何种态度面对死亡?希望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
第二部分 对于死亡主体——“我”的深思
谈及“我”,就不得不引入两个观点,一个叫“二元论”——认为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相结合的;另一个叫“物理主义”——认为人仅仅是肉体组成的,没有灵魂的存在。下面我们先详细说说二元论。
二元论既然认为人是由肉体及肉体以外的那个部分组成,如果大家愿意接受那个部分就叫做灵魂的话,我们首先可以确定灵魂是非物理、非物质的,否则便不能很好的与肉体区分开。第二点,支持二元论的人认为,灵魂控制折人们的“人格功能”,诸如思考,推理,及肉体上做出的一切有目的性的行为。第三,灵魂和肉体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当我们戳自己的手臂上时,我们会产生痛感,而痛感也会使你的灵魂感知到;灵魂对肉体的影响在于“支配地位”。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疑问:灵魂是否能永存?因为如果灵魂不能永存,那么我们仍然无法幸免于死亡,当然这也要基于灵魂存在的前提上。疑问的提出也是有根据的,我们知道肉体会死亡,而肉体和灵魂之间又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何下结论:肉体的死亡不会导致灵魂的死亡呢?另外,我们还需要二元论者给出灵魂之于人的重要性要远高于肉体之于人的重要性,否则肉体死亡灵魂存在对于个体来说将毫无意义!
一元论也就是物理主义对于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肉体。但是我们也承认,对于高阶的“人格功能”并非肉体的任意部分表达,是我们肉体上极特殊的部分做到的,也就是我们的大脑负责指挥做出一些高阶的行为。当然,物理主义也有其前提,就是人一定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系统。
第三部分 深入探讨二元论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两个持方我们应该做出何种偏向?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叫做“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即最佳解释推理。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假设二元论的存在,针对一个现象,如果二元论可以给出一个比物理主义更值得接受的解释,那么可以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
下面是二元论对于物理主义的一些攻击。
a. 人具有自由意志
b. 任何服从决定论的实体没有自由意志
c. 所有纯物理系统都遵循决定论
d. 人不是纯粹的物理系统
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但是真如二元论者所说吗?a.人确实有自由意志吗?还是这仅仅是人类的错觉?当我们面对黑和红两种颜色想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仅仅是靠自己的喜好吗?面对红色我们不仅仅是分辨到这个颜色是红色,更多的是一种感受(experience),红色代表着吸引力等等其他的内在感觉。也就是说,人们很可能自以为的主观都有其客观因素的推动。bc都各有其不合适的地方,在此不做赘述。
当然,对于二元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自证其灵魂的存在,历来哲学家们给出了很多证明,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笛卡尔的“卡式证明”。卡式证明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物体不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否则必定是两个独立的物体。以下是笛卡尔的证明:
首先我们幻想自己在一个清晨醒来,当你去洗漱的时候在镜子中没有看到自己!如果灵魂和肉体是同一的,那不能既感知到又看不到,于是论证:肉体和灵魂彼此独立。
卡式证明也具有其缺陷。我们知道每天早晨消失的最后一颗星星叫做昏星,每天晚上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叫做晨星。但是我们知道,晨昏星其实就是一颗星星(好像就是金星?),也就是满足了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条件,但并非两个客观独立的存在。所以笛卡尔的论证也并非完全正确。
不过我们不妨假设灵魂存在,然后详细谈论一番柏拉图的《斐多篇》。在《斐多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试图论证灵魂是永恒的,因为他们似乎都默认了灵魂的必然存在。首先我们补充一下“柏拉图型相”——非物质而又永恒的存在,诸如正义、公平、美、数字3等等。
循环论(灵魂永恒)
若灵魂的总和是一定的,那么当一个灵魂破碎重组后,会重新形成灵魂,这样灵魂就会永恒。显然这个观点非常荒谬,因为破碎的灵魂不一定会组成当初的那个灵魂,就像人的细胞破碎后,也许原料还仍然存在,但这些原料并不一定又合成当初的那个细胞,可能会被运送到身体的别的部位。
同类互知论(灵魂存在且永恒)
- 存在非物质且永恒的“柏拉图型相”
- 上述存在需要被非物质且永恒之物(指灵魂)认知
- 得证灵魂存在且永恒
显然柏拉图知道论证a的效力不够,但论证b又一定具有效力吗?我们研究猫的科学家一定得是猫吗?显然不是吧,同类互知论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回忆论(灵魂早就存在但并没有论证灵魂不会被消灭)
关于回忆论我们先假设自己曾经认识一个好朋友叫小明,很多年后你找到了一张和小明的合照,由这张合照,你回忆起了曾经和小明发生的许多事情。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当我们现在可以思考“柏拉图型相”的时候,也就说明早在我们出生之前,灵魂就已经存在并且就已经对“柏拉图型相”有过了解。
仍然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但是也很容易举出反例。我们在认识一条笔直的线条的时候,是不必须之前看过这样一条完全笔直的线条的,我们可以通过弯曲的线条,然后想象笔直的线条的样子。
循环回忆论(灵魂永恒)
基于论证同类互知道论和回忆论,柏拉图认为灵魂在人之前存在,在人之后也存在,可得证灵魂永恒。但显然这样的说法很牵强,我们可以想象有一辆汽车,汽车的引擎先于汽车存在,汽车因为某些缘故不能继续使用了,但是它的引擎也许可以继续存在,但绝不会是永恒。所以循环回忆论也无法说服我们。
总结一下:柏拉图等等哲学家们对于二元论的观点进行了很多论证,但在我们深入思考之下其实大多是不能成立的,但他们的思考过程是具有价值的,很多观点也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即使我并不认同二元论,但我依然尊重提出这些观点人们。
第四部分 destroy and invisible
在第四部分,我们想要讨论摧毁与无形。什么样的事物是无法被摧毁的?柏拉图认为,只有合成的东西可以被摧毁,而只有会改变的东西才是合成的东西。无形的东西显然是不会被摧毁的。
那么无形又是何种状态呢?有三种可能。第一,不可以看见。第二,不可以被察觉。第三,不可以被探测到。
于是有了下面的论证过程:
a. 只有合成的事物才能被摧毁
b. 只有会改变的事物才是合成的
c. 只有会改变的事物才可以被摧毁
d. 无形的事物不会改变
e. 无形的事物无法被摧毁
f. 灵魂是无形的
g. 灵魂无法被摧毁
当灵魂的无形指的是不可以看见时,我们可以举出音乐,音乐是看不见的,但却依然可以被摧毁;当灵魂的无形指的是不可以被察觉的时,我们可以举出无线电波,无线电波无法被察觉,但却依然也是可以被摧毁的。当灵魂的无形指的是不可以被探测时,或许我们举不出反例了,但是第二部分我们知道灵魂和肉体是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灵魂可以被肉体探测到,也就是说灵魂并非无形!
柏拉图对于自己的论证给出的结果也并非绝对,而是:灵魂几乎是不会被摧毁的(nearly)。那我们不禁要提出质疑:灵魂也许仅仅是比肉体活得更长久一点?柏拉图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和论证过程,他说事物是具有两种属性的,一种是基本属性,无法被改变;另一种是偶然属性,可以被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事物要么具备基本属性,要么就不具备。比如热是火的基本属性,所以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又热又冷的活,火要么是热的,要么就被熄灭了。在此基础上柏拉图给出论证:
a. 生命是灵魂的基本属性
b. (推导)灵魂是不会死的
c. 不死不能被摧毁
d. 灵魂是不能被摧毁的
所以,生命如果是灵魂的基本属性,那么也存在两种情况,灵魂要么有生命,要么就是被摧毁了。对此我们要针对“不死”提出疑问。不死具有两种状态:1.不能以死亡的形式存在;2.不能被摧毁。如果是状态1,那么根据火可以被熄灭,我们可以推导出灵魂也可以被摧毁;如果是状态2,仅仅是观点自证,不具有效力。
第五部分 人格同一性
分析完了二元论的观点,在我看来,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信服的,也就是说二元论并没有得到我的心证。但是我们是不能运用类似二元论的分析方法去解构物理主义的,二元论者需要证明灵魂存在,但是物理主义不需要证明灵魂的存在,而是要通过分析颠覆灵魂的存在性。比如你完全没必要证明龙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通过走访大多数地方,因为没办法走访所有的地方,发现没有龙,于是颠覆龙的存在性。当然这样的证明存在一定的不完备性,虽然我们没办法论证到灵魂一定不存在,但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灵魂不存在。
如我们上述所说,人体的功能结构是有区分的。低阶的功能我们称之为BF(body functions),高阶的功能我们称之为PF(personal functions)。显然我们对于人的定义就是要判定这两种功能哪一种的存在更倾向于证明了人的存在。
另外需要注意一点的是,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十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我吗?如果我们深究成长的变化,那么似乎人每时每刻都在改变,那么显然十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不是同一个人?这听起来非常荒谬!所以以变化为判准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讨论的是,经历这十年的主体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没有改变,则是同一个人。在此基础上,对于主体的讨论大致有以下三类:灵魂论,肉体论,人格论。
灵魂论显然还是二元论的观点,不过看起来是无法反驳的。但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上帝(或者别的什么创造出灵魂的神)将你的灵魂抽走,并且重新注入一个新的灵魂,但同时让这个新的灵魂有你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记忆、感触等等。请问:当你醒来后,你还是你吗?按照灵魂论的观点,同一灵魂,同一存在,现在灵魂改变了,甚至被改变而无法察觉!灵魂论是不合适的。
我们再来看看肉体论。首先我们要分清一点,并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构成人的必须部分。我们不会认为十年前我的手存在,十年后我的手依然存在,所以我还是我。肉体的各个部分其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也许认为掌控PF的大脑才是我们真正要讨论的肉体。但是肉体论也存在其局限性,当我们将一块坏掉的手表拿去修理,结束以后发现手表焕然一新,我们认为这块手表还是我们当初的那块吗?如果从最新买来的状态看确实是的,但如果从坏掉的状态看好像也不尽然。另外一个例子是,假设你的孩子搭建了一个积木想给下班回来的妈妈们看,但是你不小心弄塌了积木,但你为了不让孩子伤心搭建了一个一摸一样的积木,并且和回来的妈妈说这是孩子搭建的。请问:这个积木是孩子原来搭建的吗?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认同这样的事情。所以肉体论也具有其局限性。
人格论似乎是二元论和物理主义都可以接受的观点,因为灵魂也在控制着人格,所以人格论成立仿佛二元论自然成立。人格论是在强调那些更抽象的概念比如信仰、欲望等等,但你可能会说十年前的我和十年后的我因为知识储备的不同,这些概念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我们幻想一个房间里从一头到另一头挂着一根绳子,你不会指着绳子的一头说这是绳子然后指着另一头说这不是绳子,但是我们知道绳子的微观结构是由纤维层层叠叠推进构成的,所以人格的成长性我们认为也是符合人格论的。但这也并非说人格论万无一失了,我们知道有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时常会说:哦我是伟大的拿破仑!他是吗?我们假设在拿破仑活着的那一年,在纽约有一个人“着魔”了,他醒来后大肆宣扬自己是拿破仑,甚至关于拿破仑小时候的记忆也能说得出来,他也有伟大的野心想要征服欧洲大陆等等,简单来说他有着拿破仑的所有人格。请问:这时这个世界上哪一位才是真正的拿破仑?按照人格论的观点我们很难做出判断,所以只好加上限制条件(无分支原则),关于某一特定的人格有且仅有一位。
肉体论需要无分支原则吗?我们假设经过医学的研究,人的大脑是有冗余的部分的,也就是说一半的大脑即可控制整个身体并且具有所有完备的PF。现在模拟一场车祸,a的身体破碎了但是大脑保存完好,b和c的大脑破碎了,但是身体保存完好。现在经过手术把a的左半脑放入b的身体中,右半脑放入c的身体中。请问:现在谁才是a?似乎也很难下定论。也就是说肉体论也需要无分支原则!
无分支原则是在排除其余的情况,但却没有办法自证其主体的客观存在。灵魂论似乎不需要无分支原则,那他们满足了“最佳解释推测”吗?很难下这样的结论。不过也许我们在未来的成长中会逐渐偏向肉体论,或者逐渐偏向人格论,但我想哲学的意义并非是“站队”或是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思考的过程更具有魅力!
第六部分 死亡
聊完了人格同一性,我们似乎可以谈一谈死亡了。针对于肉体论和人格论,我们可以模拟两种死亡的场景。第一种是一般情况,一个正常人因为衰老死去。他的死亡是在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符合人格论)还是在尸体被火化消失的那一刻(符合肉体论)?因为如果尸体还存在,根据肉体论的观点,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他没有死亡,因为肉体还存在只是并不是一具活着的肉体。第二种是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植物人,此时他已经不具备PF,但他的肉体依然存在并且鲜活!按照肉体论的观点,仍然要等到他的肉体火化消失以后才能算作死亡,但根据人格论的观点,在这个人成为植物人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死亡了。
上述两种情形使得肉体论和人格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差,所以我们不妨在细化对死亡的判断标准,也就是人是否还具有PF的能力。
虽然我们经常谈起死亡,但我们能描述死亡的情状吗?死亡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仅仅是没有了我这个人这么简单吗?当我们无法想想死亡的时候,有的哲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人们无法相信自己无法想象的世界,即人们不相信死亡。对此有很多反驳,比如人们会购买人寿保险,会立下遗嘱,这都是对于死亡的预见。但我们在自己死亡的那个时刻还是会感到惊奇,我们无法知道死亡的确切时刻,但我们都知道人难逃一死。那么还能说我们不相信死亡吗?
虽然我们无法构想出死亡的内在画面,但死亡的外在画面我们是完全可知的,那就是这个地球上少了一个人,仅此而已。我们可以拥有从某种角度观察事物的能力,但自身完全不必亲身参与其中。你大可想象一场自己没有时间赶去参加的会议,人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一个个轮流发言等等,但是你没办法说自己就参加了这场会议。
第七部分 死亡之害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叫做“孤独的死去”,一个乍一听非常有道理的句子。我们不妨也对这个句子细细的分析一番,孤独的死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第一种可能,死去的时候没有家人陪伴。但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当一个人正常老去的时候,他的家人大概率会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不符合孤独。第二种可能,没有人和他一起死去,所以孤独。但我们也知道,在战场上经常会有共同赴死的战友,他们确确实实是在一起死去的,那么这也不符合我们的猜测。第三种可能,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去死。但在《双城记》中我们也看到为了成就别人的爱情献出自己生命,代替别人去死。这样看来“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去死”也并非没有漏洞。这时候有人提出,替代你去死的人并没有使你逃脱自己死亡的命运啊,你仍然要经历你的死亡,而那个替代你的人只是经历了他的死亡。乍一听很有道理,但是这其实并非是独属于死亡的特性。假设我去理发,这时候有个人插队说自己赶时间,希望我让他一下,我欣然同意。那么这个人是代替我理发了吗?还是按照“他只是经历了他自己的理发”?由此可见,并非仅仅强调主语便可解决问题,这只会使问题变得无聊。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我在第一部分提出的疑问做出一个简单地回答,也就是我们没办法免于死亡。但我们依旧可以探讨,死亡对于我们造成的那些负面影响,以至于我们会产生恐惧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本质上来说,死亡就是分离,不能再与外界(熟悉的人或物)有联系。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死亡之害在于一个人的死亡会对他的周遭人产生影响,大家可能会缅怀,会悲伤等等。
下面我们假设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你有几位宇航员朋友,他们在十分钟后准备出发前往火星,但是在火箭离开的二十分钟后,与地球完全失去了联系,本质上来说他们已经死亡了,因为他们与你完全的分离了,你会感到悲伤。第二种情形的背景和第一种完全一样,只是他们的火箭在升空后十分钟爆炸了,显然你的好朋友真正死亡了。这两种情形,哪一种给你的悲伤更多?
不出意外应当是第二种,因为确实死亡的事件给予了我们真沉重的打击。那么死亡这件事情本身对于我的影响是什么呢?有一种观点很值得我们探讨叫做剥夺说。死亡使我失去了机会成本,也就是我失去了变得更好的可能。我也更倾向于这种说法,因为这是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但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一件坏事吗?或者说死亡何时对我而言是一件坏事?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死亡是否有确定的时间。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假设有这样的状况,周一我开枪打伤了小明,他血流不止但没有死亡,周二我出车祸死亡了,周三小明因为流血过多死亡。那么是何时造成了小明的死亡?周三的时候我已经死亡,是谁杀死了小明呢?那么小明的死亡时间是周二吗?周二小明没有死亡,并且我没有和小明在一起甚至出了车祸死亡了。那么小明的死亡时间是周一吗?周一我开枪仅仅是造成了小明血流不止,他并没有死亡。所以死亡看起来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可如果我们没办法确定何时造成了我的死亡,我们又如何明确死亡对我造成的伤害呢?当我死亡之时我已经不再存在,死亡如何让对我造成伤害?
a. 事物只有存在时,才有可能对人有好或坏的影响
b. 当你死去时你不存在
c. 死亡对你不是坏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不再存在时,死亡剥夺了我们的潜在变得更好的可能,这是死亡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但如果我们谈及潜在的可能值得我们同情,我们就不得不讨论潜在的人类。我们都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但是精子数量庞大,当我诞生的时候,是有很大数量的潜在的人死去了,这些潜在的人也丧失了会变得更好的可能,甚至丧失了变成人的可能,他们是否也受到死亡之害的影响了呢?这里触及到了伦理学的知识,我们也不再过多讨论,但是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第八部分 自杀与对待死亡的态度
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谈谈该如何面对死亡,以及我们有没有自行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
当我们知道死亡不可逃避,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提前死亡,如果在我们判断出现在的境遇不值得我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不得不是我们提问呢:人是否有判断自己生存境遇状况的能力?衡量幸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里简单介绍以下享乐主义,他们认为幸福就是将对你好的事情与对你坏的事情加和,如果得分为正,那么就是幸福的。至于好坏事情的积分自有一套算法我们不做赘述。但如果我们仅仅接受享乐主义,其实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想象一下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虚拟现实技术,人在其中可以成为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因为技术非常成熟,人们可以体会到风雪的凌冽,虚拟的真实!攀登者的兴奋与成就感充斥着体验者的心脏,此时的他显然是幸福的,但他仅仅具有了幸福的感受,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可以接受虚拟现实中的幸福吗?(参考阅读《娱乐至死》)
当然还有另一种非常积极的论调,他们认为生命存在本身是可以给上述的幸福衡量机制加分的,也即是生命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并且会将得分拉至正向。对此我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我想这两种说法都有偏激的嫌疑,不过将幸福量化确实有助于我们分析自己的人生是否值得继续过下去。但并非看具体的数值,而要看趋势。
当我们的幸福图像一直在上升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选择死亡,但如果持续下降并且又长时间处于不幸福的状态,我们会选择死亡吗?而当我们处在不幸福的状态,并且没有自行解决生命的能力时,或许当初我们在幸福的状态下就自杀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合理和道德两个问题。它们只能存在其一,比如偷税漏税是不道德的行为,但为了企业的经营利益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指在被抓到后,惩罚的钱小于偷税的钱)又是合理的(当然不提倡偷税漏税)。那么正如上述提到,在自己既痛苦又无法自行结束生命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否符合道德呢?如果一个无辜的人,他濒临死亡但在得到医治的情况下依然有生还的希望,这时有五位患者需要移植不同的器官,我们可以“杀”死一个救助五个人吗?当在战场上,我看到一颗手榴弹扔进了我战友的战壕之中,我呼救已经来不及,只能选择扑上去挡住手榴弹的冲击,或是让我的战友死去,又该如何选择?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生命的价值就是按照数量来衡量的,但当理性和道德交织在一起时,选择的困难时常伴随我们左右。
青少年自杀的问题在当今社会及其严重,但很多时候他们的幸福图像仅仅是因为失恋、考试失利、一些糟糕的事情使得他们图像略略下凹,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可惜他们没有坚持到恢复正常的时候就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也许我没有资格说教,但是我总想着生命的存在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又怎能不珍惜、爱护它呢?面对死亡,我们不要有幻想也不要有偏见,仅仅是恰当的认识,也是最值得敬仰的!
后记
课程是最近才学完的,或多或少有些急促,但是整体上还是学到了不少知识。老师在最后谈到我们对待死亡不要有幻想,也不要有恐惧,死亡本身应该是我们的过客,过去了我们的一生也就结束了。同样,我们对待生命以及生命带给我们的快乐,又是多么应该感到庆幸!
虽然看起来非常积极,但我想死亡本身带给我们的恐惧是没办法消除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上,坏人传递恶意的方法太过简单而轻易了。我不明白他们是想通过恶来保护自己,还是纯粹想要发泄心中的无名之火。我不明白,总是善意的对待恶人究竟有没有作用。我不明白一个堕落的灵魂,一个不对对我施加暴力的灵魂,我该不该去拯救。当死亡变成筹码,世界又哪来公平?通过这节课,我明白哲学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当然哲学家们是希望能解决问题的,但我觉得思考问题的过程更值得我关注。对于一个问题的深度剖析,正是我们缺少的关键力量!我想,有时能有机会多加思考,比解决问题本身更重要。
再次感谢老师,也感谢自己能给自己一个交代。